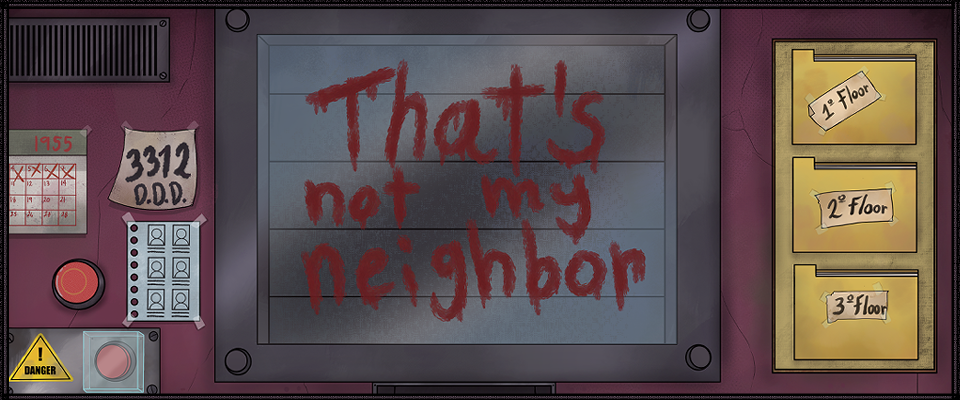
《那不是我的邻居》截图
2024年2月,Nacho Sama出品了猎奇向恐怖游戏《那不是我的邻居》(That's not my neighbor)。它的游戏机制是标准的“找不同”(Find the Differences),故事结构与《监视者》(Beholder,2016)、《请出示证件》(Papers Please,2013)等监控题材游戏较为相似,基本框架为“我”作为被D.D.D. (Doppelganger Detection Department,伪人侦查部)雇佣的“建筑物的门卫”,须不断核实尝试进入建筑物的外来者,这些外来者如与名单上的居民有所不同(无论是身份卡、长相特征还是入场申请单),在必要时就须拨打公寓内电话确认,如果确定外来者为伪人,“我”就须立刻拒其进入,并拨打3312召唤D.D.D.特工前来清除。
在游戏主播的直播宣传下,《那不是我的邻居》持续在网络上爆火,成为itch销售榜第一名,并拥有了另一个更流行的名字:《伪人游戏》(以下皆以此为简称),同时它也成为各种小程序找错类游戏[1]的素材常客。该游戏的公寓房客牛奶工弗朗西斯·莫斯(Mosses Francis),因其伪人反差特质还引来大量同人创作,伪人游戏甚至衍生出二创歌曲《Open The Door》[2],以及与其他IP联动的热门鬼畜视频。
伪人的相似/相异体现为游戏过程与游戏图像的双重性:“我”不断重复着相似/相异的检查证件信息的动作,以决定放过/阻拦外来者进入;游戏中的伪人也以相似/相异的视觉形象频繁出现而让人难以辨识。大量主播的相似/相异视频素材和(found footage)陈片再制的鬼畜形成传播过程中的第三重自相似(self-similarity)。
相似/相异的反复滑动正是伪人症候的核心特质,同时也是各种小程序、轻体量、热门恐怖游戏的共同变化趋势:传统恐怖游戏的设计准则是箱庭或背景堆叠的氛围感,而当下热门恐怖游戏的设计准则开始走向“把规则怪谈转换成了找不同的直观玩法”[3]。这种简化方式是将怪谈规则本身的抽象化为实际的游戏玩法,不再通过氛围感塑造恐怖性,而是通过相邻物件比对唤醒相似/相异的识别,从而形成流动三角下的美学体验:即“陌生-恐怖-熟悉”之间的反复循环。
身处其中的我们,最后处境也落脚到游戏标题所言的《那不是我的邻居》中被遮蔽的相邻文义上:从一开始“我”(玩家)与建筑中的住户就不是邻居。与一直想要进入其中的伪人相比,“我”才是真正的外来者,那么为何游戏的标题又要强调“不是”的特异性呢? 也正因为相似/相异者被困于游戏的相邻界面内,缺少立绘的“我”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身份,才在反复检查中坠入眩晕(vertigo)并乐在其中。
不过,一旦伪人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形成有母本/摹本的对象关系,就会即刻触发弗洛伊德所提到的恐惑(uncanny)效应,并进而生发出对异己者的恐怖/恐惧的双相情绪,暴力也随之转变为杀戮。即便最后清除了相似/相异者,形而上学认知失调症(Metaphysical Awareness Disorder)也会一直萦绕其中,在伪人游戏的噩梦模式中的“我”也得了此等症状。而相异又相似的是,身居网络社会中的“我们”与同一赛博空间里的用户也并不是物理世界里的邻居,只是超扁平(superflat)下的过视(overvisual)幻觉数据;但在视觉上我们又都是相邻的存在,然后成为不断增殖的无限清单(vertigine della lista)的分子之一。
相似/相异/相邻共生而成的伪人症候早已充斥这款游戏,并流溢到精神症状、现实历史与网络空间的互文之中,伪人实体亦在神怪、赛博与肉身中反复膨胀腾挪,这也是本文将一一刍议的内容。

《那不是我的邻居》二创歌曲《Open the door》
一、相似的伪人:滑稽、浪漫与恐怖
只要两个人物身体的相似度到达难以分辨的程度,其中一个就可被认为是伪人,甚至本体可以不必出现在观众眼前。鲍德里亚则将其称作非假体替身(Non prosthetic standing),它的萦绕让“主体既是他自己又不像他自身,当非替身假体实体化、可视化”[4],就意味着死亡从原初场景中被释放,进而杀死本体。
伪人形象的本质就是“存在两个同时活动、可能相互排斥的人物,他们会对某个人物本身或周围环境产生令人惊愕的直至阴森可怖的影响”[5]。故而孪生者、镜像者、分身、水仙(Narcissus Complex)、第二自我(alter ego)、蜡像馆、克隆体、复制品、平行空间者等不同类型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伪人文学主题。在漫长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伪人经过了从滑稽性到浪漫性再到恐怖性的三重美学转向,这在《伪人游戏》中都有所体现。
伪人形象一开始并不直接导向恐怖美学,而是在滑稽美学中起到视差的功效。最早的伪人作品来自公元前206年,是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创作的《孪生兄弟》。在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伪人这一概念被再度挖掘,莎士比亚在《错误的喜剧》和《第十二夜》中就进行了对伪人的滑稽形象的创新[6]。伪人在此阶段更多是表现不同身份、相同样貌的人在相异生活环境中“出糗/整蛊”而带来的喜剧效果。普罗普就认为“行为/身份的重复,会使它丧失创造性,从而变得可笑”,模仿则更加强了重复现象的外部特征,进而将严肃作品进行解构讽刺。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伪人的心理学转向了对自我分裂的探讨,神经学家奥拉夫·布兰克(Olaf Blanke)提出三大自我幻觉[7]的自视性幻觉(autoscopic-hallucinatio)研究就是代表理论:一个人即便只能短暂地看到自我形象,就已形成位面(planes)伪人影像。此阶段里,伪人作为第二自我的投影,是对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强烈被抛离感的弥合,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有相同样貌却互不相识的个体的存在,能极大程度地抚慰这种被原子化、碎片化的自我孤独感。无论是《两生花》(The.Double.Life.of.Veronique,1991)、《情书》(Love Letter,1995),还是《年少日记》(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2023),该类作品都秉持一种双生者/伪人对另一个自己跨越时空的共情。
现代伪人形象拥有恐怖性特质,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浪漫文学家让·保罗(Jean Paul)1796年出版的小说《西本凯斯》(Siebenkäs)。作者在该作中创造了“Doppelgänger”(伪人)一词,它也曾被译为替身、同行者、双影人或二重身。[1] 霍夫曼(E.T.A.Hoffmann)则成为该时期对伪人主题最感兴趣的作家,曾经在15部小说中塑造了伪人与本体在相遇时所面临的自我性消失和分裂性失控的焦虑。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伪人中形成“对所有认知理论的怀疑”[8],并在此环境中逐渐走向自我异化的结局,成为一种“被打碎的、多次投射的、失去方向的症状”[9]。
伪人也由此逐渐拥有取代本体的行动特质,而不仅仅是对相似者的状态描述。如果“双影人”只是强调相似性带来的混淆,是名词性状态(a≈A);那么“二重身”则更具有攻击性,成为伪人的动词性状态(a→A)。二重身可被理解为濒死体验下的离体自窥症,这原本就是器质性病变患者在濒死时出现的以第三人称回顾自身人生的走马灯现象,并由此引发“当自己的二重身出现时,就意味着本体被伪人所吞噬、死亡并被取代的过程”的文化怪谈。这也是《伪人游戏》中伪人想要通过接受“我”的盘查而进入建筑的根本动机,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取代本体。
不过在街机模式里,伪人与本体的相异性非常明显,在游戏的开头过场动画里就谈到“伪人具有变形和冒充另一个人的能力;但是一些伪人可能并不擅长,可能会出现瑕疵”,这种瑕疵显而易见,导致伪人作为刻意失真的拟像(simulacra),变成仿造(counterfeit)人类面目的异形。它们也往往以与人类三种相异的形态出现,分别是局部元素的堆叠(如眼、齿、空洞、虫等)、错位(如疤痕、眉色、痣、鼻等)与扭曲(如面部、手、口腔、浮肿等),它们都萦绕(hantologie)在期待通过窗口验证的身体中。
这些细微的相异性,首先带给玩家的就是身形扭曲的滑稽感,冒名顶替(qui pro quo)性也正是西欧古典喜剧的范式之一,或者可以用网络热词“欢乐谷效应”加以解释,当不适感情绪堆叠到一定程度后(大量出现的伪人),人就会开始莫名追求欢乐,这正是一种自然生发的喜剧感。随着“我”不断进行游戏的重复动作,滑稽感逐渐退场,转变为对伪人与本体肖似却无法入场的同情:其中有不少伪人入场并非那么让人迷惑,只是发色转换、痣的方向、鼻子大小、衣服条纹的细微差别,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无法被许可入内。这些伪人形象在后续游戏检查里越来越抽象,也由此触发了恐惑(unheimlichkeit)效应,它们变得越发怪异而让人毛骨悚然(creepiness)。恩斯特·耶特斯(Ernst Jentsch)就曾提出威胁模糊理论(TAT)与分类模糊理论(CAT)解释人为何会感觉惊悚。所以并不是伪人本身让人恐慌,而是因为识别系统失灵导致无法确定是何类别与害怕程度,才让人感觉恐慌。

《那不是我的邻居》不同伪人模样集锦 图源B站UP主三三得九九八十一
二、相异的辨别:非生非死的幽灵
在《伪人游戏》里,除了用视觉辨别是否为伪人的差异性以外,还有另一种在现代社会才会熟悉并采用的方式,那就是文件检查:身份证(ID卡)、入场申请单和公寓清单缺一不可。
在游戏过程中,被一遍遍用以参考的公寓住户照片是以黑白色复印件呈现在玩家面前,但意图进入建筑的外来者却都是彩色的,其中相异的细节只能依靠照片下方的文字描述才得以构筑并被辨识。但无论伪人还是人类,他申请进入的理由都无法成为“我”拒绝/允许的标准,而是回到图像的相似/相异上进行判断。于是“我”在游戏时不断检查外来者与清单图文时,基于图像的视觉逐渐被基于文字的言觉所褪色又再度清晰。
随着持续比对彩色与黑白模样的过程被循环启动,德里达式的从“身份证照(photomaton)化形为幽灵证照(phantomaton)”[10]的过程也被反复召唤。这二者构词法的相似性是德里达在语词修辞中的惯性操作,即由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em)对文字/书写中心主义的取代,人们“绕着这个东西”在说话的时候,发音过程中的滑音便会唤起相似音节词,使其逐渐具有谱系连贯性,并进而生发出“被劫持的言语”[11]。德里达通过对文字符号本身的延异(diffērance)而不是原有记忆的还原,取代了相似体物理上的相异(différence),重新回到命名上的相似。
在《伪人游戏》中,随着“我”对公寓住户基本信息的逐渐熟悉,伪人与本体共用同一姓名让命名相似逐渐失效,这就使“我”在检查时再次回到视觉的相似/相异上。身份识别上的黑白色照片成为死亡与静态的表征,成为伪人之外的“非生非死”的幽灵形象。而幽灵“本质都是一种幻象(phantasma)”,是幽灵证照(phantomaton)的另一种延异,是对“人类精神结构的稳定性和影响自身的自然性”[12]的质疑。
如果说“找不同”游戏的本质是从相似中寻找细微差异,并且将其标记,当所有标记被识别之后,游戏就宣告结束。这是一种更加理性稳定的区分方式,并在识别过程中完成了自我认同与结构稳定。那么《伪人游戏》就是将标记之后的行动继续推进,最后以消除相似物的结果完成游戏。而这份自我认同随即陷入被随时可能出现的全新复制品取代的危机中,伪人只需重新更换细微的像素图层,又可以相异的躯体再度登场,继续被动等待“我”的检查。
这也体现在“我”的两种看似相异的对待伪人的操作中:
一是当“我”误将伪人放入建筑后,人类邻居的死亡并不会被即刻发现,而是在最后结算数量时被告知“二次”杀死。且当“我”第二次误放伪人进入后,屏幕后会伸出一双幽灵双手蒙住“我”的视线,游戏也会立刻以失败结束;二是当“我”将伪人拦住、拨打电话后,D.D.D.特工会在有卷帘门遮挡的情况下清除伪人,但倘若错拦了人类,墙面上则会出现幽灵面孔。
无论是哪种幽灵形象,都并不存在本体,却依然可以随时在场/缺席:“我”所面对的伪人与本体之间的相似/相异过于细微,以致在公寓清单未被标记本体之前,仅依靠“我”对正常人类应有的想象无法直接判断真伪。拉塞尔·雅各比在《杀戮欲》里就指出,弗洛伊德在考察unheimlich(陌生)/heimlich(熟悉)的构词关系时,就从其相似/相异出发,指出这是由“对细微差别的自恋”(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带来的强烈敌意与对抗[13],无论是我对伪人的,还是伪人对本体的。
同时,整个建筑物门卫只有“我”与游戏中唯一出现的员工亨利,亨利是业已死亡/发疯的个体,而“我”是无法看见自我游戏形象的幽灵玩家(这在大量的“找不同”游戏也是如此,“找不同”者只是一个游离于游戏文本之外的幽灵视角),是作为见证者(martyr)证明伪人曾经存在并尝试进入建筑物而已。
于是这一批评中,同时出现了原本不应共存的三个相邻主体:伪人/本体都渐次想要进入建筑而被阻拦检查(进入者主体);检查者作为自我形象缺失的外来者,他所凭借的依据是黑白公寓清单(监察者主体);最后消灭伪人的D.D.D.特工是无法识别面目的全副武装,且消灭过程也无法被看见[2] (清除者主体)。最后这三者在“那不是我的邻居”这一陌生化表述中达成了不可能的互视:“我”看到了自己的被看,凝视着自己的被凝视,却早已习惯于重复的检查操作这一规训。

《那不是我的邻居》噩梦模式古神全图鉴 图源B站UP主 Byyy琪酱
三、相邻的并置:在附近共存的敌意
在游戏风靡将近5个月后,作者又推出了噩梦模式。在该模式下,“我”的职业身份已从“建筑物的门卫”变为“星际圈的门卫”,住在公寓里的本体(正常人类)也被涂抹上各种宗教恐怖要素,成为“古神居民”[14]。但这一切都是“我”在扮演门卫角色时所做噩梦而产生的幻象世界。此前尚在想象界的伪人拟像成功占有了玩家的精神状态,成功入侵现实界。
《伪人游戏》里伪人也越发接近异形(alien),这未必是伪人的真正模样,更有可能是被认为是异己者后的污名化,即便这些人都是“我的邻居”,它们已经被“我”所异化(alienation),相似/相异的评价标准也在噩梦模式里逐渐模糊,伪人与我的相邻变得更加接近。这种设置的改动也愈加接近另一个伪人怪谈的流行作品,《曼德拉记录》(The Mandela Catalogue)中所描述的替身者(alternate),其类型也更为模糊,分别为似人者、神明化身与异常肉身。
在神话故事里,“敌意才是孪生子关系的标识”,邪恶也并不是从神灵实体中生发,而是从“将他者物化并惧怕他者”与“对次要差异的威胁”中滋养的:彼此之间的对称性带来了“那令人憎恶的一致”,使得嫌恶与敌意的“沉淀物”最后变为狂热与仇恨,进而形成“这怪物般的精神生活”[15]。
而“我”又何尝不是在重复劳作检查中异化为了机器的相邻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变得“与个体对立、对个体漠不关心”,进而把个体当做“可抛离、可重复、可交易的商品”[16]。机械化的人类没有敌意,而是沉默并沉溺于大量矩阵复制品所构筑的法西斯美学之中,在“人群的集结、人的物化、物品的增生或复制”[17]的庆典中,将愉悦、狂欢与暴力交融起来。
于是,无论是自己还是想要进入的古神/伪人/本体,都成为了邻人此物(The Neighbour Thing)。
就如齐泽克所说:“那种引发同情、使酷刑无法接受的(受折磨主体的)邻近性(proximity),不是酷刑受害者的纯粹物理的邻近性,而是在其最根本处邻人的邻近性”[18]。无论这个主体与你的相似/相异程度有多少,因为他于相邻处存在,就会引发可知觉的共情。所以在《伪人游戏》中出现的双重非物理性的相邻性,正是作为阻断相似/相异共情的“/”(slash),相邻才是证照(媒介)、是非生非死(边界)、是幽灵(膈膜)本身。
第一重相邻性是透明性。“我”与进入者之间永远隔着一道窗口/屏幕,它形成了人体不可逾越(infranchissable par le corps)的距离,保证伪人在未进入建筑前无法对“我”造成实际伤害。同时也让“我”可以在视觉上检查伪人的相似/相异性差别,而不是在听觉上获得他想要入场/离场的理由。这才是“我”与伪人成为敌对者的根本原因,因为“敌人是一个你对其故事一无所知的人”[19]:只要“我”在透明性的另一侧(依然是相邻),就可以不用对话而是以言语(盘问)切断进入者的主体性,并在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s)中完成检查。
第二重相邻性是区隔性。在“我”拨打电话让D.D.D.前来后,处理“被我认定的伪人”画面在窗口处被卷帘所区隔,没有任何被屠戮的镜头在游戏中被看到,直到不属于这一系统的要与“我”玩卡牌游戏的小丑出现。在他反杀特工之后,窗口再度打开,“我”才能看到其被肢解后仅存头部的画面。这一过程如戴锦华所言,是在完成“区隔异质性的人群”,通过“归纳、筛选,最终达到某种纯净,形成某种由纯净造成的美感的过程”[20]。但不可视不意味不存在,游戏界面的标题正是如血书一般留下的语言痕迹“那不是我的邻居”,这又是何人所写?是“我”、伪人还是本体呢?
双重相邻性不仅让“我”/伪人存在视差,同时也存在音差(difference tone)。进入者的理由讲述并非全无声音,而是由大量无意义的滑音组成,听者无法读取任何有效讯息。这些噪音的幽灵在场(the spectral presence of noise)使玩家听到的不只是诡异,还同时存在外来者的神秘。噩梦模式中的古神居民则让音差更成为背景设定的一部分,并再次以可听却无可辨识(unrecognizable)的方式阻断了“我”继续沟通的可能。
格罗斯(Jan T.Gross)的《邻人》(Neighbor)就呈现出这一症候,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并不完全是来自纳粹德国士兵的屠杀,而是那些同在一个小镇波兰邻居下手进行[21],并且他们还会秉持与“我”同样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理由,以受害感(victimization)的方式脱罪。

《那不是我的邻居》参考作品《天外魔花》。图源 The Game Theorists
4、余论——相涉的投射:被解密的现实
在噩梦模式里,有极低概率登场的头套男(即街机模式中的小丑面具男),在出场时会给我塞一张纸条,上面给出了另一个讲述D.D.D.的“真相”。纸条上有“不要相信他们”的字样,以及“IT NOW”(它即此在)的五进制相互转换的密码,解密后会在网页里得到一份绝密文档,讲述隐藏在幕后的作为军事行动的特洛伊木马计划与主导者阿夫顿博士(他就住在公寓3楼)的过往:这些伪人并非外地生物,而是被人为制造的,用以模仿并取代人类的实验体,它们“完美复制语言、身体同化有待提高、却依然无法遵从命令行动”。这就导致部分伪人逃离研究基地,于是基地里的D.D.D.才会前往抓捕。换言之,伪人其实并非想要进入建筑物居住,而是进入建筑中躲避追捕。
能得以佐证的是,在游戏结算面板里会显示各项数值,伪人是被D.D.D.捕获的(captured),而邻居是被杀死的(killed),即伪人并未真的被清除,而是重新投入实验改造,从而达成其取代其他人类的目的。绝密文档还显示,这一计划实施于1945年,它正好夹在两部作品中——电影《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46)与原版小说《夺尸者》(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44),讲述的世界观如出一辙。在现实时间线上,英国也有类似的面部整形特工计划,用以应对可能提前到来的冷战。同样是直到1945年,该计划才被军人詹姆斯·哈奇森(James Hutcherson)所揭露[22]。
1945年同时还是全球首枚原子弹爆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伪人畸形学(teratology)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战场的大量机械化武器让人类的各身体部位更容易受到伤害,被毁容的士兵从战场退下回到生活后,因为各种丑陋的身形与面部而备受歧视,他们成为19世纪印象主义对“丑”的具象化,也就是破相者(les Gueules cassées)。
战争制造了大量伪人,他们的涌现让美国原本流行一时的畸形秀(freak shows)很快失去市场,因为畸形不再是表演,而是现实。1984年,纽约州集市奥蒂斯蛙人秀也成为美国最后一场畸形秀。
与此同时,1945年后核影响带来的身体变异报告(尤其是日本)也逐渐增多,并且几乎不可逆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此后核恐惧(Phobia of Nuclear Weapons)如影随形,不只是核武器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所滋生的怪物想象(如哥斯拉),还有(如切尔诺贝利、福岛核泄漏)核泄漏带来的对身体严重影响,出现各种变异现象。
这一切在“我”眼中就是伪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面部的扭曲变化上。伪人在游戏中的面部身形越发扭曲,正是寓意着这份时空相邻性的衰减,将相似性的断点不断拉扯,直到变成更加陌生的相异性。
进入千禧年之后,这种相似/相异/相邻性在现代生活中早已极其普遍,我们所处的网络空间也早已伪人化。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早已相当成熟,肉身的轮廓界限早已被取消并成为视觉平面的贴纸,声音皮肤(voice skin)与声音克隆(voice clone)的泛滥更是层出不穷。即便其声画都是真实素材,浅层伪造(shallowfake)所采用的“加速、再剪辑、拼凑、BGM干扰”等蒙太奇手法也依然大行其道。
所以,从比对中不断寻找相异性、从叠加中不断规训相似性,从网络中不断增生相邻性,是游戏内外共同的现实生态。就像那些不断出现在各种游戏直播切片、二创视频和其他小游戏的变体伪人一样:这些没能进入建筑物的伪人早已进入网络窗口,成为了素材;而一直在建筑物内的本体也早已逃离出屏幕,成为了观看者。

《那不是我的邻居》同名音乐剧 作者:Random Encounters
注释:
[1] 在抖音、微信有各类热门小程序游戏,其中一种为找错型,与找不同型有微妙区别,为采用各种点触型道具发现被伪装的游戏真相,其中以脑洞天花板、隐秘的档案、文字派对、整个活吧、玩梗高手等游戏为代表。
[2] 该曲作者为Longestsoloeve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3wzOJa-kPM),在YouTube播放量已破千万,并登上B站音乐素材排行榜前10长达2月。
[3] 藻起. “怪谈”游戏的出路,是“大家来找茬”. 游戏研究社. [OL], https://mp.weixin.qq.com/s/AZ7i_HPKvCxM7t4RYNefRw
[4] [法]鲍德里亚. 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M].王晴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p145.
[5] Elisabeth Frenzel. Motive der Weltliteratur[M].Stuttgart: Alfred Krner Verlag, 2008.p93.
[6] 赵蕾莲. 双影人主题透视的现代危机[J]. 学术交流, 2019(9):p178.
[7] 其他两个分别为出体经验(out of body experience)与离体自窥症(heautoscopy),这三种自我幻觉都和大脑的自我认知和感官错位相关。详见Sarah Zhang. The neuroscience of out of body experiences. [OL]. 杨睿译. 利维坦:https://mp.weixin.qq.com/s/6KK8Ez7WoozYHWdFF0IeXg
[8] 赵蕾莲. 论克莱斯特中篇小说的现代性[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p92.
[9] [法]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p222.
[10] 李洋. 雅克·德里达与幽灵电影哲学[J]. 电影艺术, 2020(3):p5.
[11] [法]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张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p12、305.
[12] Sébastien Rongier. Théorie des fantômes [J].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6:p188.
[13] [美]雅各比. 杀戮欲[M]. 姚建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p v.
[14] 一楼的居民名字可能来源于圣经以及相关的神秘学著作,二楼的居民名字全部来自克苏鲁神话,三楼的居民名字来源于除以上两者的其它神话体系。详见B站up主@小返不说慌 视频解说: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M4m1r7uF
[15] [美]雅各比. 杀戮欲[M]. 姚建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p169-170.
[16] [美]杰弗里·尤因. 《异形》与哲学:我寄生,所以我存在[M]. 穆童,张磊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9:p71.
[17] [美]苏珊·桑塔格. 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选[M].黄梅等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6): p90.
[18] [斯洛文]齐泽克.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唐健,张嘉荣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p40.
[19] [斯洛文]齐泽克.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唐健,张嘉荣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1):p41.
[20] 戴锦华. 空间与阶级的魔方[OL]. 社会科学报: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6/10/372806.html
[21] 杨T. 格罗斯.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中犹太群体的灭亡)[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9:p121.
[22] 详见The Game Theorists. You Are The REAL Monster In That's Not My Neighbor![O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p_hdU9u9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