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天皇:“天无二日”还是“共享天下”
中国皇帝“天无二日”,日本天皇却可与武家等势力“共享天下”,这一观念差异造成的是,历史上日本的“万世一系”和中国的“改朝换代”。换句话说,就是日本顶层权力(天皇)的相对稳定,和中国顶层权力(皇帝)的不断变动。
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权力超级大,但他的麻烦也大。他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甚至有时还有“道德楷模”)“集于一身”,即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林毓生所谓的“universal kingship”。它的牢不可破就在于这“三位一体”,但它的脆弱或软肋也在于这“三位一体”。如果你没有权力当然不行,如果你不再神圣或者道德有亏也不行,如果让人看出你是无知无识的傻瓜更不行,人家就会推翻你。因为下一个想当皇帝的人,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代表了道德,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推翻你。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五德终始论”,新皇帝在推翻老皇帝,建立另一家另一姓政权的时候,除了说自己有德、替天行道,也完全可以用火克金、金克木、木克水、水克火这样的理论,来证明改朝换代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大家都熟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说的,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也表现了传统中国的一个常识,皇帝不见得永远是一家一姓。“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面对秦朝皇帝,刘邦和项羽虽然一个垂涎三尺,一个跃跃欲试,但都是想掀翻秦始皇,自己当皇帝。当了皇帝的,像刘邦看到底下整整齐齐地跪了一大排官员,就喜滋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没当成皇帝的呢?传说中黄巢就愤愤然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或“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有日本学者统计过,且不说像走马灯一样,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换了多少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历代近两百个皇帝中,篡弑废立,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被杀掉的(31人),就是自杀的(6人),还有在压力下被迫退位或被废掉的(33人)。
而日本的天皇呢,虽说“万世一系”多少有些夸张,但他们不像中国那样讲嫡长子系,只讲亲缘关系;不讲政治伦理,只讲血缘神圣。这使得它的连续性很强。按照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讲,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也是拥有天照大神亲自赐予三神器的彦火火出见的子孙。这种血缘上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所以天皇是神性(文化)的象征。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拥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权力,为什么?因为日本还有很多血统高贵的贵族,像古代的苏我氏、物部氏,以及中世所谓“藤橘源平”四家之类。这当然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乃是由各个地方豪强家族整合形成的有关。尽管六至七世纪也就是日本国家形成时代,天皇一族确实强大,所以才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加以神圣化,所谓《纪》《记》的神代传说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日本的天皇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所以,到815年修《新撰姓氏录》,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得给一千多姓氏确立来源、搭配神祇以及明确等级。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想象中的神灵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构造成互相匹配、秩序井然的一个等级社会。
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是“贵种”,但不是唯一的“贵种”,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镰仓时代幕府掌权以后,天皇主要只是作为文化象征,而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则可能属于另一些传统的老贵族或崛起的新贵族,也就是幕府将军以及守护各地的贵族大名。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和中华帝国的“一君万民”专制统治比起来,日本“万世一系”强调的只是天皇家是“贵种”中的“贵种”。不过这也好,这个往往并不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天皇,虽然始终是神圣象征,但只要不像13世纪的后鸟羽上皇(ごとばてんのう,1180-1239)那样为了夺回政治权力,要跟幕府干一仗,平常倒也不那么碍眼和碍事。把天皇搁在京都当作神圣象征,底下的实际政治权力,就由武将们自己去争夺,谁有本事谁当将军。从建久三年(1192)源赖朝(みなもと の よりとも,1147-1199)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武家政权以后,镰仓时代的北条、室町时代的足利、江户时代的德川,至少在文化上还尊奉天皇,就当其是永远的神,在京都那个地方养尊处优,写诗作画,接受崇拜,仿佛《庄子》里说的那个被供奉在太庙里的千年之神龟,井水不犯河水。一直到时代巨变,或者有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或者出了一个天才的有力天皇,比如像明治维新时期需要强人的时候,他才会横空出世。
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好像一样,中国皇帝诏书中,自称是“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也自称是“明神御宇天皇”。一个说是“天”,一个说是“神”,但在实际的政治中,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还真是千差万别。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就说帝国会有两个中心这件事,中国向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就算是有——当年我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挖空心思在历史里找,像北宋一批退休官员以司马光、程颢为中心住在洛阳,用思想文化批评开封(汴京)的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一帮人用政治权力搞改革,形成所谓两个中心,但毕竟洛阳只是退休人士,远远不能和开封的皇权相比;明朝永乐迁都北京,虽然原来的首都南京还有留守的内阁,但是终究比不上北京,只不过是个影子内阁;清朝的承德和北京,有国外学者认为一个象征十八省中国的首都,一个象征内亚地区满蒙回藏的中心,但实际上,毕竟还是同一个皇帝在管着。
可是在日本呢?还真是“天有二日,民有二主”。近世日本为什么会有京都作为天皇的王城,而江户作为幕府将军的实际重心(中世是镰仓)?渡边浩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说,东京的上野叫作“东叡山”,与京都的“比叡山”相对;东京上野有宽永寺,京都东山有延历寺,都是用年号作寺庙的名称;德川家康死后,不仅日光有东照宫(也称作“东照大权现”),居然也和京都的天皇一样,被视为“天照大御神”子孙。本来照理说,幕府将军乃是代天皇执政,象征的只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天皇则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象征的是神圣和文化。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都被分化了,这成了日本特别的政治文化传统。就算天皇不服气,想重新掌握大权,像前面我们提到的13世纪后鸟羽上皇,他不甘心大权旁落,想掀翻当时的幕府,造成所谓承久(三年)之乱(1221),那也不行,甚至《平家物语》中,居然把天皇举兵说成是“当今(今天皇的)御谋反”。“御谋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人们甚至有这样的看法,天皇代表的不是公权力,毋宁说是私权力,你要反过来夺权,就成了“谋反”,尽管你是天皇,“谋反”之前要加上一个“御”字。到了关原之战(1600)后,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关白、太政大臣,他利用天皇的权威,除了形式上对将军的任命之外,已经掌握了几乎全部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叫作“公仪”(こう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有“公仪”,但江户幕府更加强有力,所以叫作“大公仪”(おおこうぎ),但它仍然没有与公家彻底分离,天皇还是名义上的日本地位最高的人物。
当然,这种文化神圣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分离,也造成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是最终谁才是真正的“神”?谁才是真正的“天”?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还好办,一旦出现危机,就得重新调整。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这个矛盾就出现了,西南边缘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藩,就借了机会“尊王攘夷”,把幕府推翻,推天皇出来,这才开始了明治维新。我想,这里可能隐含了一个很现代的政治意识——我并不是说,这就是现代政治意识,而是说这可能是导向现代政治意识的传统资源——即领袖、国家和政府,在理念上应当分开。就像当代的日本,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党竞争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手上,但国家的象征则是天皇。天皇不那么有权,这没关系,他只需要神圣;总理大臣不那么神圣,也没关系,他只需要有权。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一旦某一极出现真空或失落,另一极就会填补上去,像幕末时期将军不灵光,就把天皇拱出来掌权,重新收拾山河一片。当然,这种结构的弊端也在这里,有可能导致谁也不负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曾经指出,日本这种没有绝对坐标的思想和没有统一构造的传统,导致在日本(包括天皇与官僚、民众)政治文化中,缺乏主体责任心,形成所谓“无责任体系”。一方面,“天皇/帝国”至上的所谓“国体”,构成所谓爱国主义情感,支持着一切价值,使得每个人都没有应当负责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所以,一切以“爱国”为名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天皇、幕府(或官僚)、民众三者,各有理由对政治行为不负责任:处于顶端的天皇,可以认为这一切是下面推动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愿,所以没有责任;官僚则认为,所有政治举措都只是服从上面的旨意,我不过是履行职责,也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责任无关;而民众则认为,自己没有进入国家统治体系,只是跟随爱国主义情感,所以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
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谁都有理由“甩锅”。这就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无责任状态”,它使得日本政治有时候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
忠诚与叛逆:政治伦理的绝对与相对
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差异,导致了政治伦理原则的绝对化和相对化。
怎么说呢?传统时代所谓政治上的忠诚与叛逆,在中国和日本是很不相同的。丸山真男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忠诚与反叛》,就是讨论日本政治和法律中有关忠诚与反叛的难题,以及这种政治伦理在日本历史上的变迁。我的理解是,在日本,由于“政出多门”即权力结构是重层的,而不是一元的,因此在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伦理往往不像中国那么清晰、严格和绝对。你如果注意到日本所谓“忠诚”,实际上有对天皇的忠诚(文化意义上的),有对将军的忠诚(政治意义上的),还有对主人的忠诚(日常社会中的),就知道这种忠诚是多元,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反过来,这也导致了“叛逆”难以界定。丸山真男引用有贺长雄(ありが ながお,1860-1921)《日本古代法释义》中的疑问,举出承久之乱、南北朝内乱和明治维新三个历史事件为例,说明日本的忠诚和反叛相当复杂。像“承久之乱”中的后鸟羽上皇,他是不言而喻的天皇(甚至是三位天皇的父亲或祖父),可是,由于起兵讨伐幕府,却成了“天皇御谋反”,也就是“反叛”。可是,幕府将军挑战天皇,像北条义时(ほうじょう よしとき,1163-1224)打败后鸟羽上皇,把老天皇流放隐岐群岛,自行拥立茂仁王为新天皇(后堀河天皇),在日本却又不算“反叛”。所以,丸山真男无奈地说,有时候“对朝廷而言是谋反,但从幕府角度看又不算谋反”。
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多元,造成政治伦理价值的分化。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日本封建性主从关系中,接受“御恩”的从者,就是要向主君“奉公”,也就是要有为主君“献身”的忠诚,但这只是在法律秩序崩坏时代,依赖人格的忠诚而形成互相依赖的私人关系。对武士来说,武士和藩主之间,好像也是一种儒家所谓大义、名分的君臣关系,感觉上就是“生死的命运共同体”。也许,大家听过《忠臣藏》的故事,就是德川纲吉时代,四十六武士(原本有四十七人)为藩主浅野长矩报仇,杀死导致浅野之死的另一个藩主吉良义央,最后被幕府裁定,全部剖腹自杀(此事发生于1703年)。这四十六人在日本被认为是“义士”,这一事件呈现了日本“法”与“忠”,也就是政治与法律、伦理与制度之间的冲突。这一故事是真事,这四十六个人的“忠”,只是对主人的,没什么特别的是非,要按照中国的说法,它就是“愚忠”。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说的“愚忠”?就是不识大体。那什么才是“大体”?在中国就是三纲六纪,最要紧的就是忠于王朝和皇帝的“道德”和“伦理”。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忠诚只能奉献给正统王朝和绝对皇权。所谓“孝”,只能对你的生身“父亲”,对其他人就有问题;所谓“忠”,只能对本朝的“皇帝”,而忠于其他人(像诸侯王、藩镇)就不行。这是绝对的和严格的。也许,这与中国的“父系制度”相关。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西周的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绝对重要,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直系“父子”的继承制度,“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这种“立子立嫡”的单线血亲制度,决定了生父只有一个,皇帝制度决定了君主也只有一个。“天无二日”,所以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上只有“一”,没有“二”,更没有“多”。这造成了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有所谓“正统”之争,天下只有一个是“正统”,其他都是“异端”,不可能并存,所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那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二,古代中国才会发生所谓尊生父还是尊皇父的争论,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就是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大事件,因为无论是父子还是君臣,都必须占有血缘和政治上的第一优位;第三,由于王朝与君主的政治伦理,是绝对的、严格的和清晰的,所以,古代中国才有所谓“贰臣”和“遗民”问题,“贰臣”就是在政治伦理上不绝对忠诚,朝秦暮楚,“遗民”就是政治上不根据是非、强弱,而是根据“旧朝”还是“新朝”或“旧君”还是“新君”,决定自己的绝对认同。当然在特别的时代还有一点,即统治者究竟是来自哪一族群,是汉族还是异族,这决定臣民是认同文明还是服从野蛮。这本来也是“愚忠”,但它的“忠”是绑在“国/朝廷/皇帝”身上,因此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立场看来,这就是“识大体”,懂得大是大非。如果从传统中国的伦理价值观来看,日本武士把“忠”绑在“主人”身上,似乎只是小是小非,好像和中国政治伦理有点儿不太一样。当然,中国政治伦理的“忠”,也还是附着于某一张“皮”上的,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所以,后来顾炎武看到这一点,就说究竟是“亡国”还是“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才重要,你不能因为一家一姓的“国”亡了,就觉得绝望了,要是“天下”也就是文化亡了,那才是真正的绝望。这当然是后话。
可是在日本,正是由于天皇、将军、大名,都不能绝对拥有道德的权威性和政治的制高点,甚至血缘意义上的父母,也并不一定是绝对忠诚的第一对象。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天皇和贵族的继承,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兄弟、儿子甚至还有妻子,甚至还有养子、赘婿。按照日本学者所说,中国的“父系制”和日本的“双系制”差别很大。所以,有关“忠诚”与“反叛”的政治伦理就会分化,远远不是那么清晰。不仅如此,政治、文化、道德也可以“分化”,他的“忠”,不必只是对“予一人”的天皇,忠诚可以对幕府将军,也可以对地方上的守护大名,甚至也可以对直接的主人。“只知有藩主,不知有将军,只知有将军,不知有朝廷”,似乎在传统日本是很常见的。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荻生徂徕(おぎゅうそらい,1666-1728)就曾表示,比起京都的天皇来,江户的将军才是国家的真正君主。而各地的大名也一样有舍命效忠的死士。福泽谕吉说,明治维新前日本三百多个诸侯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所以,很多行为不见得在政治伦理上就一定是你死我活、此是彼非,不是忠臣就是奸臣,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但是在中国,一个王朝一个皇帝总是拥有绝对的、完整的、排他的政治合法性,只有对皇帝的忠诚,才有正当性和道德性,皇帝是最高道德和神圣象征,你就得“忠”,你也得“孝”。反过来,如果你叛变某个王朝,就是“贰臣”(比如洪承畴为清朝立大功但仍是“贰臣”),反对某个皇帝,就是“大逆”(比如方孝孺之被诛十族),甚至为了社稷安危暂时拥立一个新皇帝,也成了“罪过”(比如明代的于谦)。
日本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实现了“大政归还”,表面上权力与权威都集中到了天皇身上,这个时候,忠诚与反叛逆绝对性才转移到对“天皇”、“皇国”和“天朝”身上。正如已故的飞鸟井雅道(1934-2000)指出的,明治政府一方面接过了推进维新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负载了普罗大众与维新志士们的忠诚。当他们接受“尊王”的时候,他们确实拥有了极大的权威,但是当他们为了日本近代化而开国,这又与“攘夷”的立场对立,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看所谓“明治三杰”的命运,长州藩士对大村益次郎(おおむらますじろう,1824-1869)的刺杀,西乡隆盛(さいごうたかもり,1828-1877)的叛乱与自杀,纪尾井坂之变中士族对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としみち,1830-1878)的刺杀,其实正反映了明治时代国家权力从“双重体制”和“重层结构”转换为一元化集权(“古代中国化”)时期,“忠诚”与“反叛”,也就是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我曾提醒说,中国史研究者忽略了明朝的一件大事,这就是前面提及的15世纪,当明朝的皇帝(英宗)由于“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1449),大臣于谦(1398-1457)居然可以另立新皇帝(代宗),而且还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理由,这其实是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古代儒家总是宣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因为权力来源都是皇帝,所以传统时代的君主其实并不轻。可明朝中叶帝国危机时期,由大臣另立皇帝,这里所谓“君为轻”,其实已经瓦解了皇帝的神圣性和绝对性。但是,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上,这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例。通常,中国皇帝还是绝对权威,于谦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在英宗复辟后,也得被杀死。对于皇帝的忠诚与反叛,对于王朝的捍卫与谋反,在中国常常成为判断绝对是非的尺度和界限,除前面提及的“贰臣”外,口语里面的“叛徒”“三姓家奴”“汉奸”“反复小人”这些词,就让你知道这种政治伦理的绝对性和严厉性,在中国是何等厉害。
入什么祠堂、进什么庙,被冷猪肉供奉,还是跪在门前,让人吐唾沫。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依据某个似乎神圣的合法性政治权力来划线。
革命与改良:“改朝换代”还是“咸与维新”
中日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差异,也许就影响到两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不同路径。
中国皇帝垄断了全部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大凡要做大改变,必须整个推翻。也许,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往往需要“改朝换代”。也就是人们说的“换人做做看”,而无法真的“咸与维新”。在古代中国,儒家表面上很崇尚“禅让”,觉得尧舜真是伟大,可以选贤任能,其实,这种可能性根本是很小很小的。有的学者从文献记载上研究,觉得中国改朝换代有好多是“禅让”,像曹魏取代后汉,西晋取代曹魏,还有像南朝的宋齐梁陈。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让位和推辞,都是做做样子的,因为权力就是一切,它不仅意味着财富,甚至还联结着身家性命。所以,一旦某人掌握了全部权力,手下的人就会全部180度大转弯,赶快上“劝进表”,使了劲儿说明你伟大,不光是权力应当归你,文化也是你高明,道德也是你完善,所以你就应当是皇帝。然后呢?这个掌握实权的人假装谦让一下,就顺水推舟当了皇帝。像后来的宋朝取代后周,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好像不得已被推上了这个位子,其实也是做做样子,本质上还是打下来的江山,终究还是换了新天地。然后依照传统,大臣和史家就开始塑造伟大光辉的皇帝形象,把原来旧皇帝在政治文化宗教上三合一的伟大与光荣,全部转移到新皇帝身上,再加上编造出身的神话,不是说皇帝他妈妈梦见什么龙附身,就是说生他的时候红光闪现,天降祥瑞。
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赋予一家一姓一个皇帝的这一传统,决定了要促成大变化必然要彻底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更何况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不光有血缘和姓氏的差异,不能让给外姓,让给外姓,就等于彻底改朝换代了,特别是,还有族群的差异,一旦皇帝从汉族变成异族,或者从异族变成汉族,不是“以夷变夏”就是“以夏变夷”。按照前面引用顾炎武的说法,就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这也许就是晚清不能“君主立宪”,而非得“种族革命”的缘故之一?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晚清的自我变革,变不出太多的花样,就是因为大清的天下,比中国的天下更重要,亡中国可以,亡大清不行。清皇室其实心底想的,就是一家一族的权力很重要,你不推翻他,他根本不会自愿“逊位”,那份《清帝退位诏书》在自愿交出权力的背后,其实,恰恰是对移交权力的满心不情愿。
中国是东亚第一个共和国,这很值得骄傲,但这种从帝制到共和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激烈革命的历史基因,即所谓“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只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说法,以及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口号,就是这种激烈革命的思路,不能全算到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头上。由于生存在“改朝换代”就会“断子绝孙”的恐惧中,旧政权总是会用极端方式捍卫王朝。而这种激烈革命的基因,中国有,日本却很少。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法垄断一切,因此他也不必包揽一切。血缘不能分享,但权力可以分享。所以,日本最终还是在边藩、武士、改革者,以及外部压力的联合包围之下,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中国所谓“虚君共和”,在日本倒是实现了,反正它的天皇未必能垄断一切政治、文化和宗教权力,现代日本有了宪法,有了政教分离,有了议会制度,天皇虽然还是万世一系的神,但他在文化象征上的意义,还是远远大于政治权力上的作用。
所以,你得注意中国和日本政治文化,尤其是顶层权力层面的差异。中国皇帝的权力远大于日本天皇,中国是“绝对性的集权”(予一人、寡人、绝对或普遍王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历史上虽然有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但按照已故田余庆先生的看法,这只不过是历史上偶然的“变态”,常态还是皇权独大,门阀“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已故的刘泽华先生也说,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皇帝独一无二,皇帝是“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的“五独”,具有“天盖式的权力”。秦汉以来,最后到清朝,发展到见皇帝要三叩九拜,甚至臣下对皇上要自称“奴才”。很多学者就认为,这是传统中国之所以难以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王权的所谓“(朝廷与幕府)双重体制”或“(天皇-将军-大名)重层结构”却不同,天皇也罢,将军也罢,大名也罢,虽然是世世代代传承不绝,但他并没有这么绝对性的权力。日本天皇虽然万世一系血脉绵长,明治时代神道与天皇之结合,也证明了天皇之神圣性与他的血缘谱系相关(这一点在明治宪法中有明文规定),但日本天皇的合法性来源与中国皇帝仍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国的“天授王权”,必须加上有“德”才能获得天命,有了比较强的儒家德治主义,所以,不符合“德”则不能得“天”之护佑。这不仅给“革命造反”或“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也导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造反有理”,要把皇帝拉下马,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可日本“天皇”却不会被“革命造反”或“改朝换代”,无论幕府掌权者怎么变化,从源氏到北条,从北条到足利,从足利到德川,不变的是天皇。山崎闇斋(やまざきあんさあい,1619-1682)曾经说,就算天皇是没有“德”的无道之君,可是因为他被传承了三种神器,那他就是“有德之君”。为什么?因为“此神器与玉体一二无分别故也”。所以,他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神祇。尽管也有天武系和天智系的不同、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的争执,但大家乐得拥戴他,因为无论他有没有“德”,他反正是神圣血脉下的子孙,他反正是“神”,而且他也没有实际的巨大的政治权力。
当然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天皇一点儿用也没有,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其实,尽管法律上天皇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但是因为他在文化上的神圣意味,他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调整政治取向的微妙砝码,有的时候也能通过文化影响政治政策。我们不妨看幕末时期日本从“锁国”到“开国”这一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从思想史上看,这时水户学逐渐兴盛,“尊王攘夷”的说法影响了日本上下的观念。恰在这时“黑船来航”(1853),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向日本提出“开国”要求,这对“锁国”已经数百年的日本是极大的事情。幕府征求意见,当时各大名提出的意见书约60通:其中赞成开国的也就是“开国论”有22通;不屈服于无理要求、不赞成开国,但又希望避免战争的,也就是“避战论”是18通;认为必须严守锁国体制的“锁国论”是19通。其中,前两种看法占了40通。幕府根据这个结果,于第二年(安政元年,1854)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给船只提供燃料和食品,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据日本学者尾藤正英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幕府的权力削弱,而是意味着幕府的政策得到大名的支持,反而增强了幕府的立场。
但是,天皇虽然只是虚位,但也并不完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接下去的事态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发生的消息传来,幕府内部对与美方签订进一步协议有些犹豫,于是,1857年幕府将军派堀田正睦(1810-1864,接替刚刚去世的阿部正弘担任老中首座)去京都征求天皇的意见,但天皇并不表态,堀田正睦空手而归。这时,近江彦根藩的藩主井伊直弼(いい なおすけ,1815-1860)担任大老,大老虽然是虚衔,但掌握实权的井伊却在这一年擅自与美国签订了《日米修好通商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这个决定没有得到天皇的批准,使得幕府的立场很尴尬:一方面没有得到天皇之命,违背了“尊王”的精神;一方面擅自轻易与美国签约,又违背了“攘夷”的精神。于是这来自水户学的“尊王攘夷”,反而成了攻击幕府的“公论”。这一年,在京都的孝明天皇给水户藩送去密件,征询各个大名对于幕府将军此番处置的意见。原本处于虚位的天皇这一异常举动,居然无视幕府的权威,最终使得井伊发动“安政大狱”,严厉处罚反幕府的人士,这导致了第二年(1860)水户藩的脱藩武士在樱田门外刺杀井伊。这一事件之后,幕府再也无法独断专行,不能不与天皇(朝廷公家)和诸大名妥协,并终于形成所谓“大公议所”(类似国会)和“小公议所”(类似地方议会),在这种“公议”下,这才有了后来德川庆喜在二条城召集藩主们决定的“大政归还”,也才有了此后的“明治维新”。
有趣的是,明治元年(1868)作为新政府方针公布天下的《五条誓文》,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以公论决万机”。在这一事件背后,你可以看到幕府、天皇、大名之间的博弈,也让我们看到“政出多门”之后,权力之间就有了移动和制衡的可能性。显然,走向近代过程中的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中国皇权那样高度集中的独裁或专制。一人独裁或专制的结果,往往就是皇帝与王朝、统治者与国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本不可能有妥协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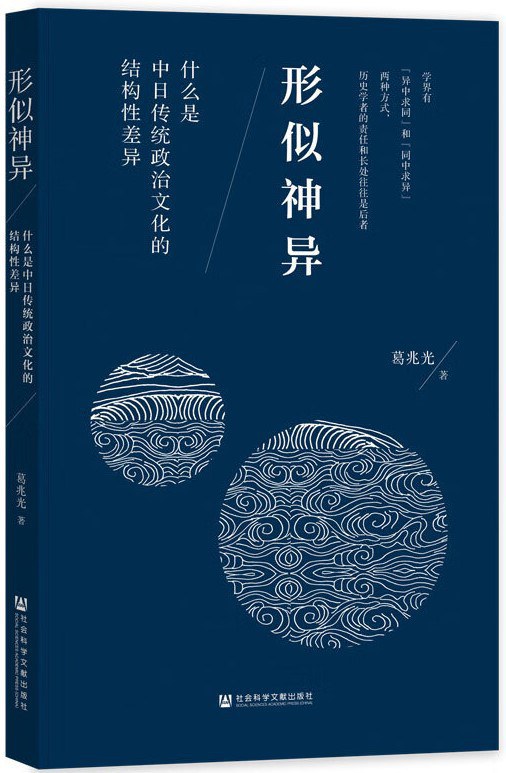
(本文摘自葛兆光著《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